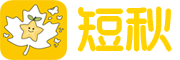春香
雨在窗外滴点地下,声声脆响,进入我耳中。
日子刚刚过惊蛰,雨季也多了起来,那天,我像往常一样,穿过巷街,街中人多,行行往往不绝。
我肩挂书袋,手靠着青墙,刚才差些被旁边拉车的车夫撞了,等我站稳后扶了下眼镜,车上的主人已经下来了,过来看我有无被伤到。
我低下头一会,抬头看时,主人早已经从车上下来,是位姑娘,穿着贵装,模样瞧着约似二十。
“怎样?”姑娘轻口开问,我却看到她这样子,一下了明这是谁家的小姐,自己则是位有志而身穷的生员。
“无事,多谢小姐的关心。”我低下头像羞了一般躲开姑娘的对视,心里祈祷只愿快些离开。
“那好。”姑娘见我这样,也就直了腰板,脚根一抬,便要回车上。
我见车夫逐渐走远,也就起步重新走。
走进学堂,雨丝还未断,坐在书位上,我脑中竟有着那张模糊不清的脸,我想,也许是心在燥热吧。
自那日后,我穿过巷街,总要看是否有那日拉车,为此,我不少开始被同窗给嘲弄,看着窗外发呆。
只是事转在一天正雨,那日,刚下学堂,我定在学堂檐下躲雨,我捉急,手无一把油纸伞。
我捉急之时,恰好看见一辆拉车停在学堂门口,而车帘突然被拉下,一张多日浮现在我脑里的脸此刻现身在我眼前,是那日的姑娘小姐。
我看着她一时身子难动,而她好像是下来来学堂有事,接过油纸伞,打开,下车。
我目视她进了大门,她似是看到我,但也就一刻,等候就漠视我深入。
雨还在下大,而我眯眼皱着眉头,只觉得这雨真的下不是时候。
等我听住一道声音,朝着声音方向看去,那姑娘已同师长一起向门口过来。
而我看到她,心里只觉疑惑。
“先生,这么大雨,是无把伞可挡?”姑娘可能是看我还定在学堂门口未动,过来问我,我明白她是认出我来。
听着姑娘的那话,我依旧低头没看她,她见我这模样,笑的竟有些温柔。
“先生,上日在巷街差恰撞住你,今日再往学堂中偶遇,咋不说是缘分呢?”我有些出神,嗅着空气当中那淡淡的雨绣味和丝风般的清香味,不敢与姑娘对视。
她的话中,有些尊敬我?这简直让人诧异。
也许是见我还不要说,又是开口:“若身真无伞,上我拉车,载你一程。”姑娘此话,让我的心口猛地一停,随后快跳。
我最终还是跟着姑娘一同上了拉车,车间狭隘,坐着二人实在紧。
我一路中还是不敢与姑娘对眼,只怕一眼,便无法挪开眼,也许就是因为二者阶级不同。
待到巷街街口里,我便告知姑娘,先行下车。
下了拉车,拉车的车夫冲我一笑,却没有什么话要讲,我也理不清头脑,但看车夫与拉车越行越远,我也就抬步回至家中。
那姑娘生的太媚人了,我心里暗想,近几日被她燥的睡不入梦,连坐在学堂内也无精气神。
数日过后,那姑娘张脸还在我脑里,占据比知识多,是胜过的。
但命运就好像要看我和她,在雨季不再来时,我又一次与她相遇,只是这次,我已经离了生员这个身份。
那张脸已然模糊,我不再梦里见过,只有朦胧。
再次遇到她,是在正月的火车站,天气还凉,我随便呼出一口气,肉眼可见。
正月,我正好要踏入归乡,在外求学数年,现如今学有所成,自然便想归乡教书。
入幕,贴着绿皮的火车随着烟斗吐气缓慢结束,在我眼前停住,我提着行箱随着人群进入了火车内。
火车内,我找到自己的硬座坐下,双眼在车间扫视一眼,清一色的都是穿着长袍或西装的新青年。
我只是看了眼,便转头望着窗外,只是这一眼,我就瞬间身子一停,火车外进车的人群里有一位特别。
她与众不同,穿着一件绣着龙凤纹的金黄旗袍,头丝又束成半扎,显得有种古韵的美,只是身边陪着一位穿着黑灰长袍的男士,二者亲密,后面还跟随着两位仆从,都牵或抱的护着小娃子,其中一位女管家抱着一名女婴,看上去好似才刚刚满月,被另一位女管家牵着手走的男娃,样子也不大,就三四岁,幼脸嘟嘟的。
我看到那位旗袍姑娘,愣住,心也停跳,但我眼睛认出她来,身子比我先一步认出她,我难掩激动,但知道自己与她本就没必要。
她和相公一同进入前一列,我只是默默的看她进去,又随着车列员的关门而消失于我的视野中。
之后一路上,我心绪难说,以至于下了火车后,我依旧难受,也许这件事,我要用往后更多日子去释怀。
春香,源至于你的芳香,源至于惊蛰过后,误遇你,误动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