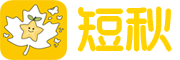蝉.小思
礼拜六,照例是迟起的日子。揉开睡眼,时间已近11点,幸好是白天,才不至于让我深陷伤感之中。拉开窗帘,用几分钟适应阳光的强度,瞥一眼变幻的车水马龙,仿佛一场无声的动画,白花花地刺眼,显然,世界早已忙碌多时了。
今天的主线任务依然是获取2000大卡,我便骑了电动车,要去吃那家熟悉的兰州拉面。这面馆我已光顾过许多回,以至于老板看见我,不等点单,便兀自去下厨照旧了。车轮碾过柏油路面,发出轻微的嗡嗡声,我坐在车上,竟如坐在一匹识途的老马上,不必驾驭,它自会循着惯常的路径前行。
我的身子在车上,魂灵却不知飘荡何处。眼睛望着前方,实则视而不见;手虽扶着车把,却不过是做个样子的傀儡。行人来来往往,我机械地避让;红灯亮了,便停下来,绿灯亮了,又向前行。一切皆按部就班,既无意外,亦无惊喜。我的躯壳在上海的街巷穿行,内里的“我”却仿佛抽离出去,悬浮在半空中,冷眼旁观着下面这个骑电动车的陌生人。
这光景,竟像是乘了一辆会自动行驶的车子,不必费心操控,它自会载着我奔向既定终点。我的生活何尝不是如此?日日上班下班,吃饭睡觉,一周复一周,竟成了不必思索的循环。在世间,我不过是一粒微尘,随着人潮涌动而涌动,随着世事变幻而变幻,自己倒成了最无关紧要的存在。
正胡思乱想间,忽闻一阵尖锐声响,刺破了我麻木的感官。细听才知是蝉鸣。这声音起先是一只,后来竟引来了三五只的应和,聒噪得几乎要撕裂这城市的喧嚣。我抬头四顾,才发现路旁梧桐树上,这些小生灵正在用尽全力地嘶鸣。
我刹住车,静静倾听。这蝉声何其熟悉,却又何其陌生!幼时在乡间,每逢盛夏,蝉鸣如潮水般涌来涌去,我们是听惯了的,甚至嫌它们吵闹。而今在这水泥森林中,突然听到这生命的呐喊,竟使我悚然一惊。
想起小学的文章《蝉.小思》中说,这些蝉,潜伏地下数年,甚至十数年,方得破土而出,爬上高枝,蜕壳振翅,为的不过是这短短数周的鸣叫。它们用尽全身气力,嘶哑了喉咙,也要宣告自己的存在。而我呢?我有口却不愿歌唱,有眼却不愿细看,有耳却不愿倾听,只是浑浑噩噩地度日,仿佛生命是可以无限挥霍的财富。
我忽然羞愧起来。这些日子,我活得像在自己家的围墙上踱步的猫,以为世界不过是我脚下的尺寸之地。我忘记了天地之大,竟不只有我一人存在;万物之盛,竟不只有人类一种活法。那蝉在地下苦熬多年,才得见天日;那路边的野草,从砖缝中挣扎而出,向着阳光生长;甚至我每日吃的那碗拉面,也是农人种麦、工人碾粉、厨人调味的成果。这一切,何尝不是生命的奇迹?
风忽然起了,吹过街树,拂过我的面颊。我这才注意到,路旁花坛中竟开着不知名的小花,红的黄的,虽不名贵,却也自得其乐地绽放着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,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,随风晃动,宛若活物。
我终于到了面馆,今天换一碗汤面,热腾腾的牛肉面端上来,雾气氤氲中,我忽然品出了不同于往日的滋味。那面条的柔韧,那汤头的醇厚,那香菜的清新,竟都鲜活起来。我慢慢吃着,不再像往日那样狼吞虎咽,只为填饱肚子。
归途上,蝉声依旧时断时续。我却不再觉得它们吵闹,反而听出了生命的节律。我的电动车依然如故,但我已不再是那个麻木的骑手。我开始留意路旁的风景,感受风的温度,观察行人的表情。
原来活着,不只是呼吸吃饭上班睡觉,更是要打开所有的感官,去体悟这世间的万种风情。哪怕是最平凡的日常,也藏着无数生命的奥秘与感动。
那只蝉或许不知,它的一声嘶鸣,惊醒了一个都市人的迷梦。